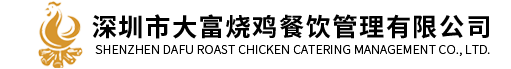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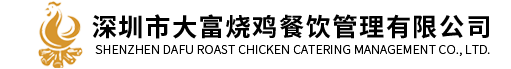
取消
清空记录
历史记录
清空记录
历史记录
乐鱼|【边界观察】全英最热门食物,不是炸鱼薯条,不是中餐,为何竟是印度菜?
【“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田野调查经历,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自伦敦往西,沿大西部铁路一路行进,不到半天便可到达德文郡的郡治埃克塞特(Exeter),从本地的圣戴维斯火车站走出,拥挤的停车场被四周零星的商铺所包围,一间名为“卡尔玛”的印度餐厅是能遇到的第一间餐馆,紧挨着古朴的大西部旅社。
到达英国之前,我曾在一本旅行手册上读到印度菜已经取代炸鱼薯条(fish and chips)成为全英最受欢迎的食物,着实让人感到意外。要知道,炸鱼薯条的大名早在我小时候学习《新概念英语》时便已耳闻,难以想象这样一道英国国宝级的菜肴居然会输给印度的“舶来品”。
 “卡尔玛”餐厅的印度菜。拍摄:赵萱
“卡尔玛”餐厅的印度菜。拍摄:赵萱埃克塞特是一座只有10万左右人口的小城,但据2019年7月的网上统计(trip advisor),这里居然存在至少23家印度餐馆,尽管不少英式餐厅都会提供炸鱼薯条,但主打炸鱼薯条的餐厅却不到5家。
在本地的钟楼一侧,有一间以“炸鱼薯条”命名的小型餐吧,极不起眼,但这却是本地最有名的炸鱼薯条,可我几次路过都见其大门紧锁,门上挂着“闭门”的牌子。一天临近中午,我见到一位中年男子抽着烟,斜靠在门口,便上前询问餐厅是否营业,男子回答道:还没到时间,还得20分钟。于是,我便与他攀谈,才知道他就是餐厅的店主,而他每天遵守着严格的营业时间,午餐仅在中午12点-2点提供,而晚餐则是在下午4-6点。这是一家40多年的家族餐厅,几代人共同经营,而营业的宗旨让人印象深刻:支持本地的渔业和农副业。也因此,该店所选取的食材坚持来自本地的供应商,进而希望投射出一个极富共同体感的英国本地社区与社群。
一轮有关天气的寒暄之后,我问道:“为什么这里这么多印度餐厅?是不是印度菜比较流行?”

店主说:“没错,印度菜现在应该是现在英国最流行的食物,可以排到第一。你是中国人吧?中国菜也不错,我们旁边就有一家,大概可以排到第二。”他的回答和书本上写的毫无差异。
“那么炸鱼薯条呢?”我接着问。
“炸鱼薯条嘛,还是很流行,人们也很喜欢,但是……”他左右晃了晃身子,摆了摆手,“有时第二,有时第三。”但没能讲出令人信服的原因。
临近中午12点,我问店主是不是可以开店了,他看了一眼钟楼,“还差5分钟。”
 “炸鱼薯条“餐厅里的炸鱼薯条。拍摄:赵萱
“炸鱼薯条“餐厅里的炸鱼薯条。拍摄:赵萱和店主的一番交谈引起了我对印度菜风靡全英的兴趣。早在1809年,第一家印度餐馆便已在伦敦诞生,而在19世纪之前,事实上英国人已经可以广泛地接触到以咖喱为代表的印度食物,大多由一批小型的咖啡馆所提供。例如,早在1747年,有关印度咖喱和肉饭(pilau)的食谱便已经在英国出版,由这类咖啡店的经营者所编写。
早期的印度菜品都是由以商人群体为主的印度移民带来的,例如第一家餐馆便是由一位名叫迪恩·穆罕默德(Dean Mohammad)的印度商人所创立的。在这一时期,印度菜的烹制方式大多源自家传,没有什么统一的规范。而印度菜本身就是以大量的调料和混合型的煮菜为主,这也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创新可能性,大量的英国人也开始尝试加入到印度菜的烹饪和经营中来。
在印度菜传播的初期,英国人将这些流行于咖啡馆或家中的平民食品看作是刺激性的辛辣食品,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皇室在频繁地处理印度事务的同时逐渐接受了印度菜,印度菜开始在英国的中产阶级内部传播,其刺激性的味道也被表述为别有风味的芳香和口感。
进入到19世纪中后期,由于印度本土爆发了反抗英国统治的抵抗运动,印度菜在英国的发展也随着政治局势的变革渐入低谷,直到20世纪的到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受疮痍的英国社会主动或被动地需要放下帝国的身段接受来自前殖民地以及广大世界的新事物,印度菜再次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大批从印度、孟加拉等地而来的移民和避难寻求者涌入英国,他们不仅“占领”了以伦敦东区为典型的平民社区,也挤进了英国的餐营业。
20世纪40年代,许多印度移民开始重新开办咖啡馆和小饭馆,以此作为居留的主要生计。但真正的冲击出现于70年代,从1971年开始的孟加拉移民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影响显著大于印度人的影响——实际上孟加拉人经营着当时65%-75%的印度餐厅,但印度与英国、印度菜与英国社会却因为殖民历史所带来的深刻联系而成了一条可被南亚移民广泛利用的神奇纽带。
不再是小商小贩式的经营模式,也不再是千差万别的家庭工艺,70年代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印度食品工业在英国正式出现。
英国本土一度匮乏、单调、简易的食谱在印度菜的传播之后变得多元化,来自于东方,极富传统与底蕴的香料运用智慧让英国人耳目一新。而印度的辛辣风格开始不再拘泥于口味,而是与人们身体健康相联系,例如生姜的使用。
在上述的背景中,不可忽略的仍然是强大的移民传统和隐藏其后的政策实践。1945-1975年间,临时移民劳工项目(Temporary Migrant Worker Programs, TMWP)在欧洲地区盛行,在大量廉价的、富有活力的非欧洲移民到来的同时,欧洲本土的文化景观也在发生悄然的改变。
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南亚移民群体自然而然地与英国本土的工人阶级文化相契合,而在此之前,炸鱼薯条这一类的平民食品正是这一阶级的标志之一。
如今,超过100万的印度移民生活在英国,全国有超过1万间的印度餐厅,雇员超8万人的,带来的是每年35亿英镑的营业流水和每周250万人次的客流量。早在2004年,与印度菜相关的食品工业已经在英国食品工业中占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比重,毫无疑问已成为英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伦敦拥有的印度餐厅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印度本土的孟买和新德里,并且其中有着6家米其林最高星级的印度餐厅,高居各类外国餐馆的第二位(仅次于法国餐厅),印度菜显然已经不再限于平民食品。
毫不讳言,英国的印度菜不仅比印度的印度菜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同时也比炸鱼薯条和英式早餐更能表现出英国的传统。
离开埃克塞特之前,我特意拜访了位于车站附近的“卡尔玛”印度餐厅,老板热情周到,尽管不断地接听电话,招呼着后厨,并与网络推广的商家讨价还价。餐厅的侧门与大西部旅社相通,可以直达旅社一楼的吧台,大批刚下班的铁路工人准备迎来傍晚的美好时光,而钟楼旁的“炸鱼薯条”早已停业,废弃的外带餐盒上落满油星,上面清楚地写着这样的标语:“国民挚爱”(The Nation’s Favorite)。我突然想起店主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不管怎样,人们最终总会回到炸鱼薯条。”这背后的滋味需要细加品尝。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leyu·乐鱼(中国)体育官方网站
